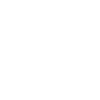摘要:顶尖科学人才的成长和培养是当前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和经济学四大科学奖获得者的教育和工作履历数据,从人才成长的全阶段,解构1901—2022 年间全球顶尖科学家成长的空间路径、区域角色与路径选择因素。主要结论为:① 全球顶尖科学家成长的空间路径具有明显的机构群落效应,取得科研突破高度依赖少数科研机构;② 教育阶段,全球顶尖科学家成长的教育中心具有显著的更迭演替现象,呈现来源的相对广泛性和流入的高度集聚性特征,美国、德国和英国占全球顶尖科学家求学流量的78.3%;③ 工作阶段,全球顶尖科学家工作的科学中心存在明显的地理转移现象,流向进一步收窄极化,被少数国家收割,美国成为最大“ 磁石国家”,占工作阶段顶尖科学家全球流量的53.7%;④ 全球顶尖科学家成长过程中的区域职能角色分化为出生型、教育型、促成型、出生兼教育型、教育兼促成型、全能型等6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美国顺势发展为全能型;⑤ 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的影响机制有其一般性和特殊性,语言被广泛证实在一般人口跨国流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对顶尖科学家迁移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文化联系中的社会制度邻近性、政治环境以及高等教育是顶尖科学家流动迁移考虑的重要因素,而目的地的科学发展水平在动荡时期对顶尖科学家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顶尖科学家;人才成长;空间路径;区域角色;路径选择因素
内容要点
人才成长过程中流动的空间路径虽然纷繁多样,但并非无迹可寻,正确认识顶尖科学人才的群体性特征,从特定人才群体成长过程中流动的空间路径倒推,执果索迹,有利于总结和发现顶尖科学人才成长的时空规律。本文对1901—2022年全球顶尖科学家成长的空间路径、区域角色与路径选择因素进行探讨,兼具现实导向与理论意义。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全球顶尖科学家成长的空间路径具有明显的机构群落效应,取得科研突破高度依赖少数科研机构。有21.9%的机构获得3人次及以上诺贝尔四大科学奖,占获奖总人次的67.4%,其中高校占比68.2%,占获奖总人次的74.8%,研究院所占比30.0%,占获奖总人次的22.1%,反映出高校、科研院所是顶尖科学家成长的关键空间载体,是其工作阶段取得科研突破的重要“助推器”。
(2)教育阶段,全球顶尖科学家成长的教育中心具有显著的更迭演替现象,呈现来源的相对广泛性和流入的高度集聚性特征。美国、德国和英国占全球顶尖科学家求学流量的75.6%。二战至“冷战”期间,全球顶尖科学家求学路径开始从以西欧为单中心的空间结构演变成以西欧—北美为双中心的空间结构,美国在顶尖科学家求学网络中的地位迅速崛起。
(3)工作阶段,全球顶尖科学家工作的科学中心存在明显的地理转移现象,流向进一步收窄极化,被少数国家收割,呈现由欧洲内部流动转向跨大西洋流动的变化过程。二战前,绝大多数顶尖科学家工作阶段流动路径集聚在欧洲内部,二战爆发至“冷战”期间,全球顶尖科学家工作阶段流动路径开始由欧洲内部流动转向跨大西洋流动,美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科学人才“磁石国家”,其吸引集聚的顶尖科学家规模占全球顶尖科学家工作阶段总流量的53.7%。
(4)顶尖科学家成长过程中的区域职能角色分化为出生型、教育型、促成型、出生兼教育型、教育兼促成型、全能型等6种。二战后,德国从教育兼促成型衰落为教育型国家,美国则顺势发展成全球唯一的全能型国家,且美国职能角色提升路径的起点始于促成型,反映出美国科学人才中心的兴起在初始阶段并非依靠本地人才培养造就,而是在吸引和集聚其他国家人才的基础上,逐渐实现“本土化”自主人才培养,并最终在出生、教育、工作3个阶段兼具比较优势。
(5)相较于一般人口流动而言,顶尖科学家流动的影响机制有其一般性和特殊性,语言被广泛证实在一般人口跨国流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对顶尖科学家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文化联系中的社会制度邻近性、政治环境以及高等教育是顶尖科学家流动迁移考量的重要因素,而目的地的科学发展水平在动荡时期对顶尖科学家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